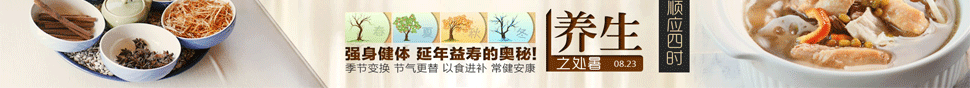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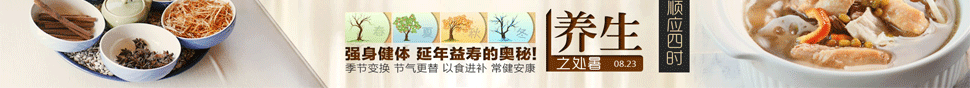
绘画王紫璇八岁
对端午节最深的印象,莫过于挂香囊了。每到这个时节,奶奶便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戴着老花镜,把艾草团团装进小小的硬纸壳,折成棕子的模样。再用红蓝绿黄等各色丝线在外面缠绕,就成了精美的装饰品。端午那天,奶奶便会把它挂在我的胸前,戴着漂亮的小粽子,闻着淡淡的艾香,我便知道端午节到了,要有好吃的了。
儿时的记忆中端午节能吃上粽子的时候很少。在我们北方的粮店里,糯米是紧俏品,如果能吃上包着红枣的棕子,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了。记得我们家习惯是吃凉糕:把糯米和大米混合,泡上两小时后,用纱布裹上两头扎紧。上锅蒸熟,就成了圆滚滚的米条。因为有粘度不好切,奶奶就用细细的线,把它勒成一个个小圆片,洒上少许白糖,一盘美味的端午节凉糕便出炉了。而我,通常是等不到上桌,便一片片捏着吃下去大半。
这是哪个地方传下来的端午美食,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每当有人问起“你的老家在哪里?”我总会略显迟疑,因为不知该回答洛阳还是西安。洛阳是我成长的地方,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在这座城市待了整整十五年。而西安是我的出生地,在那里,我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都说五岁前的孩子没有记忆力,但那段生活,却在我脑海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准确地说,爷爷奶奶是我的外公外婆,因为爷爷奶奶叫起来比姥姥姥爷亲切顺口,从会说话起,我就没有改过口。还是在我出生第八十天的时候,妈妈产假到期了,当时单位都很严格,没有什么续假之说,而爸爸妈妈那时也没有自己的房子,都还住着集体宿舍。妈妈只好把我交给她的爸爸妈妈,留在西安抚养,自己回河南上班。我从此跟爷爷奶奶长大,一直到快上小学。他们不仅给了我母爱的体贴,也让我感受到了最真切、最包容、最温暖的亲情挚爱。
都说隔代亲,这话一点不假。那时候,家家经济条件都不好,日子都不富裕,妈妈兄弟姐妹九个,所以家里更显得清贫。但是,再穷也没有苦过我。我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是,爷爷下班一进院子,就会随着自行车钤声变出一个冰棍来。小舅才大我五岁多,仅五分钱的冰棍,只有我一个人能享用。五毛钱买一笼肉包子,我吃六个,舅舅只能吃四个。后来,奶奶想办法买了只母鸡,每天收鸡蛋便成了我儿时的乐趣。当某天鸡没下蛋,奶奶便悄悄放进去一个,让我每天都能尝到收获的快乐。
西安的街道大都叫巷,跟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有相似之处。我们住的那条街叫“面巷”,记忆里,奶奶家有前后院,前院一棵无花果,后院一棵香椿树,还有奶奶栽下的葡萄藤,年年夏天,院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每到此时,我就跟着奶奶一起摘了无花果又摘葡萄,然后再跟着奶奶走家串户去送,整个面巷的人家都能品尝到来自我们这个小院的甘甜。
奶奶从小读过私塾,印象中她熟知四书五经,爱看《红楼梦》,而用得最多的,却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家里没有表,每天天不亮,她就念叨着这句话叫姨姨舅舅们起床上学。奶奶非常勤劳,全家老小十几口人,都靠她一个忙活。奶奶爱干净,爱到近似于洁癖。全家的衣服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甚至还是补丁落补丁,可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奶奶有着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温婉娴淑,而又干练。据说奶奶当姑娘时,非常有性格,在她这个年龄,女人们都是要裹小脚的,而她不愿受束缚,是一双同龄女孩羡慕的“解放脚”。
奶奶相夫教子,勤俭持家,那时总吃高粱米,但变的花样很多,有时煮粥,有时做成高粱饭,还有时蒸成高粱面窝窝。还有时用一个鸡蛋,蒸出一大锅的蛋糕。奶奶最拿手的,是用爷爷带回的菜叶,和面拌了之后放少许盐油,上笼屉蒸,一直到我上了高中,还爱吃奶奶拌的这种蒸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也是奶奶常念叨的,因此尽管奶奶对我极其疼爱,却从不许我剩饭剩菜。
大约在四岁多,我被送回在洛阳工作的父母身边。那段日子,奶奶说她就跟祥林嫂一样,看见像我那么大的孩子便呆望半天,还会跟身边的舅舅说:宝宝现在也该有这么高了吧。而我回洛阳后进了幼儿园,逢人就哭闹:阿姨,借我点钱买张火车票吧,我要回西安。
一直不知为什么,爷爷奶奶特别喜欢穿军装的人,更是支持我去当兵。遗憾的是,在我穿上军装不到两个月,爷爷就去世了。那时我在新兵连,冥冥中似乎有种感觉,于是就找机会给家里打电话,可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电话就是没有人接。后来得知爸妈都回西安给爷爷料理后事了。爷爷临终前交待,不要让我回来,让我在部队好好干。记得妈妈是流着泪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而我也是哭着听的。至今也不知道,病床上的爷爷有没有看到过我还未授衔的军装照。
年,妈妈调到北京工作,奶奶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也有了表现机会,总是找理由带奶奶一起出去吃饭。奶奶很能接受新生事物,说汉堡是肉夹馍的升级版,比萨是洋烙饼。而她最喜欢的,就是看我穿着军装的样子,说我纵使披金戴银,也没有穿着军装好看。不幸的是,年6月,医院,没想到,这一住就再没出来。
奶奶临终前几天,小姨买了张凉席给她铺在病床上。奶奶问她哪买的,小姨说门口小摊,人家要十块,我八块买来。不料奶奶叹口气说道:“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这么大热天人家卖张席实不容易,你也不缺那两块钱,又是何必呢。”怕奶奶不高兴,医院门口想还上两元钱,却没再找到那小贩,此事竟成了奶奶最后的惦记。
奶奶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91岁。
奶奶常说的那些文言文,我从小烂熟于心,却是二十年后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时,才知道它们出自《朱子家训》。也是现在才明白,这,就是她和爷爷秉承的家风吧?爷爷奶奶的一生,永远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帮助别人。这个别人,不仅有远亲近邻,还有素昧平生之人。
我一直在遗憾,他俩受了一辈子苦,要是能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该有多好啊。枝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思思,一晃爷爷去世20年有余,奶奶离去也18年了,可我从没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每每梦里相见,都如同生时一般,根本没觉得他们已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正直善良的人都有美好的明天,我坚信爷爷奶奶在天那边的生活一定是美好而悠静。
记忆中,奶奶特别喜爱前院那棵无花果。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每当夏天来临,这棵树便枝繁叶茂,结满了紫红色的果实,有些还张开了口咧嘴笑着,整条巷子都飘荡着那悠悠的清香。当兵后,我偶然学会一首歌:无花果,果无花,满园的灿烂奔放,从来没有它。没有花,只结果,心中只有别人,从没想到自我……这不正是爷爷奶奶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从此,只要听到这首歌,我的眼前便浮现出爷爷奶奶的身影,还有那个童年时生活的小院、那棵带给我们无限欢乐的无花果树,那种特别的粽子圆米条。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