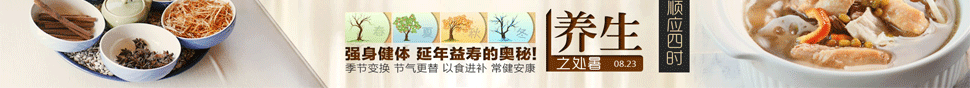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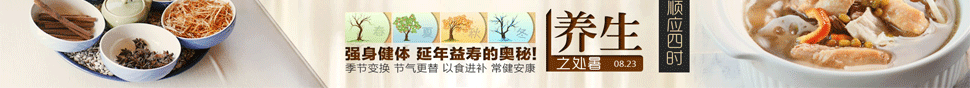
NO.26
AUGUST9
立秋啦虽然大家熟知的,广为流传的是肖邦的《夜曲》,特别是经过周杰伦的那首“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之后,基本无人不知这位钢琴诗人以及他的代表作,在不同编号作品里的一共21首夜曲。但我今天要讲的是柴可夫斯基(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英文:PyotrIlyichTchaikovsky)的六首钢琴小品中的第四首夜曲(op.19No.4)。(是夜曲Nocturne,不是小夜曲Serenade,小夜曲纯粹是翻译的偏好,然后沿用至今了。)为什么我要专门拎出这首夜曲出来呢?因为我太爱这首夜曲的大提琴版本。
老柴(柴可夫斯基)本身就是一个旋律性歌唱性极其流畅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就是有种直达心底的震动,宏大的气象和如泣如诉的细腻都可以把握到位。他为人称道的作品太多,可以记忆的点太丰富。很多旋律取自俄罗斯民间音乐,也不流俗,听《胡桃夹子》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小时候,我奶奶拿梳子沾水非要给我梳一个油头,窗外院子里黄狗吠了几声,无花果树上的鸟雀绕着树冠盘旋了几圈(无花果树汁液有毒,鸟儿不吃,也不招苍蝇)走了,地锅开了,蒸汽飘了起来,把大厅笼在了雾气里。我自己拉《六月船歌》的时候,想得绝不是电影《雏菊》里的桥段,虽然那是萦绕整部影片的主旋律(也是省事儿,省版权费),我迷恋这首《船歌》,以至于后面听到所有基于《船歌》的作品都会多垂青。
这首大提琴版的老柴的升c小调《夜曲》,我把大提琴视频(大提琴版本更推荐听MishaMisky,CorinneMorris的,女性的演奏者会比男演奏者更柔和舒畅一些。)放在这里。
速度稍缓的抒情性的行板Andante一般都是把弓子拉满,饱满且长的连弓加重情绪。前四个小节的多半音就直接把我拉进了曲子里,第五个小节呼应第一小节,第六小节出现泛音,紧接着三连音切分音,加重一种坠落的急促的情绪,然后回到三连音。后面几个小节又重复前面的部分,在尾端加上滑音修饰与灵巧的变化。怎么形容这第一部分给我的感受呢,就好像我心里有个洞,有个缝隙(虽然实际上没有),然后这一句直接像一个楔子一般给塞得紧紧的,填满了那个臆想中的洞。后面转3/4拍低音谱号,连续的双音让情绪变换,节奏也紧凑了不少。先徐后疾几个dim到crescendo的变化之后,多个六连音出现带到高潮再止息,这个用法在《六月船歌》里也有。第三部分再次回到第一部分的内容,回扣主题,最后泛音结尾。好像也没有多么复杂与绚丽,但是细节,情绪,弓法,节奏变化有很多。可能我就是无法抵挡这种半音丰富的作品。
我听歌不管是人声唱的,还是器乐演奏的,或者电子乐作品,都以旋律为主,如果这个曲不抓我的耳,那词儿都不想再去看了。在我的判断(审美)里,很多词和曲式不搭配的,如果我为了演唱一首歌曲仔细记住了歌词,那这首歌基本属于瞬间祛魅,那种吸引力和美感在认真看完歌词后而消失。所以我可以在听歌曲的时候,控制自己,只让旋律进入思考中,歌词沦为“浆糊”。虽然说音乐的种类没有界限,应该敞开心扉去听各种类型的作品,但内心还是会有个排序。这跟尊不尊重词作者无关,纯粹是我个人的偏好(来个狗头保命)。这个聆听的特点也使得我对无词歌,就是纯器乐演奏的曲子更爱一些。我可以把一首曲子听到“烂糊”,所谓的听“恶心”了,但是我绝对不会感到厌烦。不过,有例外,就是在旋律,节奏,歌词都很吸引我的情况下,这种有词歌也会成为我的“药”,确有补养效果的鸡汤。
关于不同种的乐器也有个接受度的排序,这和乐器中的隐藏鄙视链无关,纯粹我个人的接受与喜好。弦乐要好于管乐,弦乐中的西洋类和中国古典的传统弹拨丝竹也可以平坐,弹拨乐器的好处是,你只要会了一个,其他的很好融会贯通,所以我在东南亚的山村里面偶然遇见的不管长得像箜篌的六根弦,像琵琶但是只有三根弦的都能上手一弹,外行都能发出一声惊叹,什么,第一次见到的乐器也能弹奏。当然,技艺绝对不是一日之功,我只是表达这种类乐器的相通性。吹奏类的也有类似特点。当然,我心里首位的还是大提琴。他大概跟我醇厚的嗓音很配,不管什么作品改编成大提琴版本就会比原来的多了些人文,多了些鲜活。都可以变成与自己对话,若是其他乐器,大的像钢琴之类的,像是自己在操作什么庞然大物,若是太小了如笛子一般的,又有些过于潇洒。只有我抱着大提琴的时候,常常是坐定的时候,支架卡得稳稳的,弓子的来回摩擦琴弦,和我个人的呼吸声交错,好像我抱着另一个自己,这时候,哲学上的自我本我都有了,然后演奏出一个超我。
乐器和音乐作品都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纯粹是个人的审美与偏好。同时,不同乐器的不同音色和个体的遇见是一种缘分,一种宿命般的因缘际会,即使一开始选择的时候带着些中二的幼稚心理。想想多么神奇,我用乐器来代替我发声,我个人控制力度,熟练度,节奏来演绎不同寻常的作品,我可以把过去的经典作品改编,也可以自己freestyle。
最近听了很多无调性的作品,勋伯格为主,我发现现代音乐创作很多都是无调性的,特别是北欧的几位作曲家,音乐家,比如,我第一篇文章(达成“通感”的艺术作品——音乐篇)里面提到的HaniaRani(波兰,德国),还有NILSFrahm(德国),NovoAmor(英国),OlafurArnalds(冰岛),AageKvalein(挪威)和IverKleive(挪威)等。后面两位老先生的很多作品是以宗教为启发创作的,内涵却不止于宗教信仰,宗教艺术是广于,高于宗教本身的存在。有调性的音乐,或者古典乐(漫步在《图画展览会》)能深入挖掘的细节会更多,织体更丰富,无调性的遐想空间很大,符合不同情绪的宣泄。
放了那么多狗头保命,但是我想喜欢音乐的人都是自由宽容的。这次,用夏目漱石的《草枕》里面的话作结,“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时,便产生诗,产生画。”“人世难居而又不可迁离,那就只好于此难居之处尽量求得宽舒,以便使短暂的生命在短暂的时光里过得顺畅些。于是,诗人的天职产生了,画家的使命降临了。一切艺术之士之所以尊贵,正因为他们能使人世变得娴静,能使人心变得丰富。”
END
文/俺也想写云麓漫钞
图/网络
编辑/肥壤植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