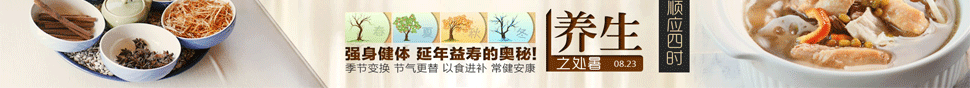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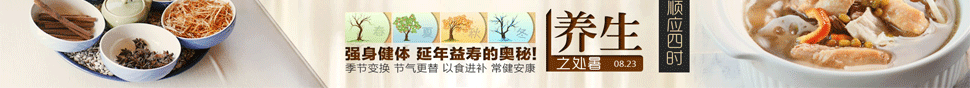
1.
几年前我在上海搭的士,耳机里放着实验音乐家JohnOswald的专辑《Plexure》,这张专辑将一些著名摇滚歌曲的经典唱段切碎后粗暴并戏剧性地拼贴,极其吵闹并难听。随身听没电后,我才发觉出租车里正大声播放着来自其公司总部及其他司机们不断发来的消息,不知是否设备故障原因,那些混杂着大量噪音的消息彼此重叠并相互打断,上海话我又听不懂(因此无具体指涉),加上诸个播报者粗细不一却同样焦躁的语调,由此同样“极其吵闹并难听”。
接着我想起来,因耳机隔音效果差,我确定刚才一直将这车里的通讯声当作《Plexure》的一部分来听。事实上,当我试着将这通讯声纯粹当作《Plexure》的下一首新歌来听,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不是想借此来解释JohnOswald的风格,而是想例举一个真实的魔术:当你的意识赋予某种非音乐音乐之名后前者就会成为真正的音乐;反之,每人都有在一些情境下将音乐当作背景噪声的经验,即,当你的(下)意识赋予某种音乐非音乐之名后前者就会成为非音乐。看,你就此成为了一名点石成金的魔法师。
不否认,JohnOswald的前卫风格令其音乐听起来极易与出租车通讯声之类的非音乐混淆,这令我邂逅获得上述知想的契机。然而,那些紧紧围绕着旋律、节奏的,所谓音乐性很强的一小撮声音是如何从一切普遍声音中拔身而出,成其为音乐?上述魔术为什么不能发生在莫扎特和屎落到地上的声音之间?或者这么问,若从人耳—人脑系统中找到并修改、剔去令莫扎特和屎落到地上的声音二元论的那些构造,是否一切声音都将是音乐,同时一切音乐都沦为声音——即取消音乐?
2.
约翰·凯奇自小就喜欢声音,但不能就此判定他喜欢音乐。就像一个孩子喜欢大海,因此长大以后成为海洋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开始,他非热爱海洋学不可。这两者的关系可看作,后者是前者遭到社会规训的后果。这个孩子也可以成为渔民,正如凯奇也可以成为一名口技演员,这些也都是对他们各自儿时喜好的社会学后续,只不过没那么浪漫或布尔乔亚罢了。若将对声音和大海的喜爱看作一种人独立、本是的性质,那么通过社会规训的分类法和系统化,无论成为音乐家和海洋学家,抑或成为口技演员和渔民,它们都将不是二人儿时喜好的实现,而是破灭。作为音乐家,凯奇的工作正是对这一破灭的实践、解释和反抗。
凯奇有用手指去敲击事物,令其发出声音的习惯。不同的事物会因此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记住并体会这些声音,这是他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些声音建立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世界的某种本质从这些关系里渐渐露出来。这是凯奇对声音的看法,也是他对世界的看法。而音乐家的身份令他必须在这种基于互指的简单看法中,极其麻烦地插入音乐。
如果声音指向世界本身,那音乐指向什么?
音乐是对声音的二元论,声音就此分为(一切)声音和只有人才能发出的声音(音乐)。这一将音乐从声音中分割出去的做法,对应于人一直致力于的,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人要去破解、战胜、驾驭自然,这一论调暗示着人已将自然从其身上推开、撇净。文明至少令这一撇净获得很大一部分形式主义实现。作为上述的反对者,凯奇要做的,反而是让音乐回归到声音里去,即让人回归到自然里去。这也是他受到“复归于无物”的东方哲学吸引所致。由此,他说:
“一个声音就是一个声音。
要意识到这一点,人必须停止
学习音乐。”
这里有一处显而易见的矛盾。人其实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自然,音乐也从来没有摆脱过声音,这种摆脱不过存在于人下意识的虚拟中。但这种下意识却客观不可逆。人并不否认音乐是一切声音的一部分,却在这一前提之上将音乐从一切声音中分出来。这一自己为自己下套的骗局是如何实现的?要识破这一骗局不能简单地调头回去,即,不能让人返回猿猴的身份去感受并承认其自然属性,他必须通过智人的,所谓人对自然的摆脱虚拟才能再次回归自然。老子“复归于无物”的“复”字的意思即在此(佛教的摆脱轮回指对自然的超脱乃至否定,它抽去了这一“复”字的前提,力求极其真诚地对“通过人去摆脱人”这一过程视而不见)。那么,音乐也只能通过音乐才能回归声音。凯奇是最激进的反音乐者,这一最字正体现在他对音乐和其本人音乐家身份的咬定之上。
凯奇的观念里最值得重视,却也可视作破绽之处,在于他必须不断确定他旨在反对、颠覆的音乐的正当性。这里非一般逻辑里建立白以说明黑,定义善以辨识恶,而是用黑去证明白所具备的黑的属性,以令你从被黑否定完毕的白里去重构白。如,海洋学对海洋的错意—栽赃正是海洋学的一个课题。这不是二律背反,而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逻辑链。没有黑色,只有极近于黑(掺杂尽可能少的白)的灰色。
凯奇说经过训练并服膺于音乐学习的作曲家“听不到他们耳边回荡的声音”,他的意思是他们听不到那些不符合其音乐规矩的声音的“音乐性”,而通过对这种“音乐性”的重建,一面令一切声音成为音乐,一方面令一切音乐回归声音。
“他们的耳朵封闭在
他们自己
想像的声音之中。”
这种想像,即对声音的音乐性的确认,正来自音乐学习。接下来,若要打开耳朵,剔除上述对声音的想像,就要确立一种“复归于无物”的“无”的聆听状态。
人们对《4分33秒》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它笔直地寓意于令凯奇着迷的日本禅学的空之类,其实它更旨在诠释《周易》里朴拙的辩证法。他反复强调、使用的寂静更接近于《周易》—道家体系里的无,而不是佛学里的空。他称寂静为“无的欢庆”;当音乐安静下来,所有的声音都因此复活。如果你坐在《4分33秒》的现场,你对其对音乐会规则、惯性的挑衅的正确回应应是,将《4分33秒》拽回到音乐会的规则和惯性中去。张开你的耳朵,囊括舞台上的绝对缄默,去听此时可能听到的所有声音。这些声音,就是《4分33秒》的确凿现场和事实音乐。
以及凯奇用从《周易》借鉴来的占卜法去作曲。占卜,即去预知将发生什么。其前提是什么都尚未发生。因此发生什么都是合理的。因此无论占卜的结果如何,你都不能当场掀翻占卜师的桌子。占卜作曲法的前提是无,是你对自己审美的清空。确保没有任何音乐残留在你脑子里,这样,任何占卜出的声音都是音乐。它没有指向好听,而仅是指向听。就像占卜的结果并不指向吉,它指向任何后果。这一后果甚至不需要事后事实对占卜预期的证实。
“无话可说,而我正在说它,
那就是诗。”
无并不是空,而是为了发生而艰难达成的一种先设,它指向一切可能性——然而,什么是“一切”可能性?凯奇致力于让音乐沉寂下来,好为被音乐消除的,真正的声音腾出位置——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声音?他迷信无,暗示没有比无更彻底的反抗——然而,无为一切做好准备,这“无”却经过了准备者之所以这样准备的原因,以及在准备过程中的历练的清洗。所以,这无并非无,而是被“有”装扮而成。它对有的指向决定了其有的本质。
剔除人性的念头并非来自别处,它正来自人性(此处人性非平常就伦理道德而言,而是指令人成之为人的“人的特性”)。如雪掩尸般,人对自然的复归是用人性在人性上面盖了一层人造的仿自然,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仅仅令伪造者本人自以为自己已成为自然中无法分辨出来的一部分。并可以这样说,那尸体上的假雪正由尸体本身生发出来。除非你对人性的剔除欲望并非来自人性,你从未将人性与自然二元分化,这一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将自己与草和鱼混为一谈。若凯奇复归于声音的愿望不是来自对现世音乐的厌弃,这一没有起点的回归所从何来?这绝无可能。这一套最后只能沦为艺术、宗教或政制这些使人更人的东西。成为一个个自噬其尾的圈套。
“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女士说,我住在得克萨斯。
我们得克萨斯没有
音乐。我们得克萨斯没有音乐的原因就是那里有
唱片。让唱片从得克萨斯消失
那样就会有人试着唱歌。
人人皆有一首
根本不是歌的歌曲:
那是唱歌的过程,
和你唱歌的时间,是
你在你所在的地方。”
结论是,凯奇并未作曲,而是作听。作为这世上最激进的作曲家之一,他却没有创作出哪怕一首有新意的曲子(“有新意”、“创作”、“创新”等等这些说法本身就不成立),事实上,他连一首曲子都没有作(就此,可以想像的比凯奇更为激进的唯一音乐场景是,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演奏其作曲作品)。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呼唤、虚构一种对人来说不曾也永不会出现的听法。简略来说,凯奇通过社会既成的音乐系统(规训—审美—创作—演奏—传播—收听)——即便是对其“彻底”反动——来制造的声音(反音乐)也只能是货真价实的音乐。其无琳琅满目;其寂静“极其吵闹并难听”。就此,凯奇所为不仅看似装神弄鬼,也确实是。但正是这样,他对音乐、艺术、文明,及人做出了无效却通透的隐喻。
3.
令声音成为音乐的,附加于声音的那种人的因素是什么?令声音具备听觉上的音乐性,如旋律,若说它体现出某种人的特质,这一特质是什么?从功用性上来说,这一特质就是人捏造的反自然性。将人从包括一切动物、植物等自然造物中神话——神性起来的部分。其神性——神话之处在于只有在人这里才能实现这一捏造。
人的自然性即天然性,再虔诚的有神论者也具备某种与生俱来的达尔文主义,对人的天然性的印象,对人之所有性质皆来自自然培育的知识先设。接着,人从其局限内可以明显辨认出人与动植物的不同所暗示的神性——人的条件。神性却并没有带给人高于动植物的处境,甚至更糟糕,否则人便不会产生出复归于自然的想法。再入世的人也想在海边坐坐,在家里养几条鱼。人为什么活得不如一棵树?这发光的、善的、令人不由自主倨傲起来的神性为何总指向阴暗的、恶的、令人不由自主绝望起来的人性?这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戏剧感,而戏剧来自剧本。至此,人的神性的本质露出来,即神造性。神性是本性,不指向任何目的,也就是说它指向包括好的目的在内的一切目的;神造性则不然,它藏着神(制造者)的居心。就此人之神性若存,亦是神造性的一部分。作个比喻:哪怕你的人的身份来自你父母一次意外交媾,你携此身份同来的人性仍逃不脱社会的布局。你既非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上,也不能天然自在地长大成人。这里有无所不在的计划、设计和控制。不期而至的你是这计划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个人、社会和自然携手成为体现人的人性质的背景、条件。
一个被造物从其身份上已被消尽了其独立和自由,但人——个人却总以为自己或多或少包含着一部分“我说了算”的自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猜,如果还有更本来的人性,它应在自然后面。在人可以体会的宇宙的后面。后面不是深处,而是之外(在宇宙之外而不是之内去谋求方法,如佛教)。凯奇意在寻求的声音和寂静,老子意在复归的自然和婴儿都既不是这些词所指,也不是这些词所喻。却也不是玄之又玄,若将“更本来的人性”解释为从人身上抽去神性—神造性后剩下的部分,它既非乌有,亦非玄幻不可道。
如果人是完全的被造—被控物,制造者显然一直在掩饰这一事实,至少不在人生理认识的局限内令人找全落实这一事实的证据。为什么不像人对待机器那样,在人显眼的地方铭上使用方法和生产日期?我想他应有这个能力,但他不愿这么做。因为这样就不好玩了。完全的被造物意味着独立性的完全丧失,从而不可能产生对制造者任何意义上的反抗。人对机器人可能会反抗人的担忧基于机器人并非完全的人造物。人只能锻造而不是制造铁。人造机器人不过是人被造的后果之一。不存在被制造出来的对制造者的反抗。或许,人不确定其完全被造性正因为人本就不是完全的被造物,制造者故意在人上残留了剂量考究的自主力和不可控性,好从中获得对其奏效的反抗。基于这一自主力和不可控性(可统称为自由意志)令人有能力向造人者发动某种程度却货真价实的对抗,其就此成为人唯一真正从制造者那里复制下来的性质,遂称之神性。而源于这一残留的神性,即便无神论者也可以时时分泌出新鲜并生动的反抗来。就像你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脾,但它一直在工作。
那么,造人者为什么要通过不完全的造人来获得人对其奏效的反抗?
人不完全的被造至少意味着人不是一种力量、一个神的完全造物。人既有可能是两种以上相互间存在分歧的力量的造物,也有可能即便为一个神所造,却在制造时混进了不为神所注意或控制的杂质。这一出现在创人的最初,可对神造成干预的,决定神对人不可尽造——不可尽控之力,即人对其神造性的反抗的来源,或称其为撒旦。人的自由意志为何不指向别处,却单单指向对神的反抗?因为被造—被控者基于其身份失去的自由只有通过从制造—控制者那里夺权才能恢复,这是一;二是,自由是好的。这一认识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撒旦。撒旦即便是上帝派来的,然而,后者虽知道前者大致会做什么,却不知他具体会做什么。撒旦正是从这里汇入人的自由意志。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造人或仅出于无聊。既然出于无聊,就要让事情变得尽量有趣一些。下棋就很有趣。作为规则乃至对手的发明者,神必需令棋局成立——安排自己有可能遇到真正的困难。为了不至于左手与右手对垒,他必须赋予作为对手的被造者自由意志。这是游戏的必要条件。棋局成立于上帝并不确定对方下一步会怎么走,但他需设法令对方下一步棋具备两种性质:令他动脑子(乐趣所在)但不至于输(身份所在)。这两者对立,上帝必须在其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譬如让对方五个子,为了更刺激,他有时只让三个子。实际上,因为贪玩上帝好几次已经输了,如巴别塔、诺亚方舟和亚伯的被杀,但他不认。
在伊甸园里,神警告人不可吃善恶果,这意味着神赋予了人选择是否吃善恶果的权利,即自由意志。撒旦派来的蛇去引诱,却不是直接令人去吃那果子,也是囿于人的自由意志。上帝和撒旦都是经由人的自由意志来对人产生作用,就此自由意志成为两眼为活式的,客观的核心游戏规则。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以令其可能代表撒旦来对抗自己。上帝、人、撒旦各自在这一体系里得到其独立的角色,正如游戏各方只能从规则里获准身份。人基于其自由意志(神性)产生颠覆其神造性并建立独立、完整人性的欲望,这一解放必须经由撒旦的帮助,于是,这里出现了撒旦通过人去战胜并取代上帝的可能,这是游戏结果之一。换句话说,撒旦在人这里成为上帝。这一过程即可视为人从刀山跳入火海,也可视为人从撒旦那里实现了其神性之外的,唯一可能的,“更本来的人性”。
4.
以雪掩尸,自然来自用人性剔除人性之后,以及让一切声音通过音乐系统才能发出,这些就是撒旦的根本方法。不是将上帝,而是将撒旦视为人智的真正出处的传统,或由此可见。冯内古特写过一句话,大致是:除了性爱之外,蛇给夏娃吃的善恶果里最好的东西,就是爵士乐。这句话不应仅用来煽情。令声音成为音乐的,附加于声音的那种人的因素,跟吃完善恶果之后,猛然令彼此的生殖器官从亚当和夏娃眼里浮现而出的,是同一种东西。它们是神性在人性上运作时出现的破绽。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那果子里的毒素迄今仍在你的脑子里发挥着毒性。不信?请仔细观察人裸体时生殖器跟身体其他部位的反差,它们如此潦草、突兀、丑陋,却仍令你止不住地想要去舔一舔;这些破绽如此明显,因为它们是上帝故意留下来给你识破的(就像密室杀人,其破绽正体现在它的不可能之上。阅读的兴趣与核心的剧情来自对永远不能破案的事先笃定)。屄屌如此丑陋,却又如此引人注目,令人心神不宁,为什么?因为它们就是上帝让你的五子。只见他双手一拢。他的意思是,好了,轮到你走棋了。
人之外的生物的生殖器与其身体多浑然天成,有些则更美而不是更丑,如花。人在猿时屄屌应没有现在这么丑,它们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依进化论而言,应来自人借其文明对它们及其作用的常年、百般藏匿、扭曲、栽赃、压抑。简单说,屄屌之丑正是对人的性压抑和性禁忌的写照。
“性交的行为及其使用的器官如此丑陋,倘若没有面容的美,亲历者焕发的光彩和迸发出来的无度的激情,自然便毁掉了人类。”达芬奇这段话被乔治·巴塔耶引用为其《色情史》的按语之一。下面后者在《论性欲》中一段话,则可视为对这一引用的男权层面的解释:“女人姣好的脸或精美的衣衫向我们许诺着脸和衣裳所掩盖的东西。脸和它的美必须被亵渎。先是揭开女人的私处,然后插入男人性器官。是的,女人的美是用来使男人感到自己身上的动物特质的显而易见和骇人的。没有人会怀疑性行为的丑恶,用来平衡这种丑恶的东西,就是美。”
同样令你勃起的,相映成趣、相反相立的美脸和丑屄构成二律背反。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的制造特殊商品的活动。而商品生产的功利性与审美的非功利性构成难以调和的二律背反。”对仗于此:“在人类社会条件下,人的性行为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性禁忌支配的性压抑下的活动。而社会用于中和性压抑的色情与制造性压抑的性禁忌的非色情性构成难以调和的二律背反。”若前一句证明一切商业艺术都是伪艺术,后一句则证明每一个具备性欲的社会人都是性变态。
据《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在吃善恶果之前已有性行为。此性行为可视为仅基于性欲的,纯洁、本来的两性关系。冯内古特所庆幸和赞美的,人从善恶果那里染上的“性爱”已不再来自纯粹的性欲,而是基于圣经所言的“羞耻”。巴塔耶他在《色情史》里这么解释羞耻,“羞耻设法以迂回的方式进入色情的炼金术……羞耻就是欲望的形象”。处女为何总是那么羞涩?因为“贞洁是一种色情”。
人将声音升级为人的声音——音乐——而令之更好听;人将性欲升级为人的性欲——色情——而令之更高涨。音乐对声音的压抑对等于性禁忌对性欲的压抑,随之音乐的好听和色情(从守贞到乱伦)带来的超性欲,皆来自这些同质的压抑。性欲通过禁忌—压抑—色情系统复归于性欲,或者说被这一系统升级为超性欲,正如音乐被人升级为超声音一般,于是人被迫成为最淫的生物,昆虫一生发一次情,哺乳动物多一年发两次情,人却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渴望并实施肏,而具备性能力在人一生中占据的时间比例,其他生物亦望尘莫及。继而,若有一位性爱世界的约翰·凯奇试图复归于羞耻心出现之前的,纯粹、本来的两性关系,他只能靠色情来剔除色情,正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女权运动或性解放运动,一切性革命都是用性禁忌去解除性禁忌(广义地说,性禁忌不止于社会禁止个人去发生某种性关系,也指其倡导乃至勒令个人去发生某种性关系)。
“经验向我们表明,正派女人若想诱惑,就会求助于妓女的装扮。”(《色情史》)在妓女那里实现的对一切性禁忌的破除虚拟(你可以让她称呼你为“爸爸”)令卖淫在最接近于吃善恶果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成为彻底的色情。色情的极端指向性禁忌之前的性关系。卖淫对反性禁忌的全面虚拟,得证并运行于它绝非仅仅发生在妓院和嫖娼之中,它也不仅发生在维多利亚的秘密里,它还发生在诸如“霸道总裁”、“壁咚”这些流行词的语义里,并毫不含糊地发生在每一副被女权运动者因故保留或因故丢弃的奶罩里。这世上找不到比卖淫更纯洁的性关系。人的一切性关系皆来自色情,所以一切性关系皆渗入一定程度的卖淫。这句话不好听,却正因此,它会令你更硬或更湿。如这句更难听的,“所有活人的一切行为皆渗入一定程度的自杀”,它或将令你活得更为带劲(冒着坠机的危险去旅游,在雾霭里更努力地工作以求早日摆脱雾霭)。这些渗入皆为人自由意志里对神不由自主的反抗所致,携着“若抱着必输的心就不必玩下去了”的游戏精神。
至于自杀——对人与上帝的游戏而言,自杀是同质乃至胜于人赢的一种情形。弃局而起,老子不玩了。即便将这弃局视为取胜,上帝亦尴尬。自杀是人对自由意志的极致使用,因其直接指向对作为设局者的对手的怀疑、不屑和挑衅。除了自我毁灭之外,人尚没有别的任何途径去完毕地实现对神的反抗(这里的实现仅指令这一反抗成立,而不是获胜)。所以几乎所有宗教都在其地狱里为自杀者留下一处刑罚至为惨烈的单元。那么,对虔诚的教徒来说,其自杀意味着他认为在地狱里受罚要比活下去更愉快,即,神对意欲自杀者的地狱威胁在他这里失效了。人正赢在这里。请注意,这种“在地狱里受罚要比活下去更愉快”的判断正来自之前的活。也正是之前的活,令一个无神论者决定通过自杀来将自己掷入完全的空无,正如凯奇用音乐的那一套去制造寂静。自杀是人通过活向活添加的一种人的特质。无论自杀指向地狱或寂静,被70个赤裸处女围绕的快乐抑或“更本来的人性”,这些死都是人性对活的分类,都是活的构陷。
杨波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wuhuaguoshu.com/whgzp/4672.html


